【正見網2010年05月12日】
我和師父是二十年前認識的,有幾年的同事緣分。
由於工作關係,我受了點外傷,手臂一直疼。有個同事告訴我說師父厲害,會氣功,能調病,就帶著我找師父。辦公室裡,師父在我手臂上來回劃拉了幾下,也沒什麼感覺,疼痛就減輕了。那是我第一次和師父接觸,知道師父懂氣功,能發功。也從那時起,我開始關注這位新來的年輕人。
師父高高的個頭,常穿著半新不舊的灰色運動服。在單位裡平平常常,不顯山不露水,和大家一樣。工作上也不顯得太突出,也不落後。單位裡練節目,師父把森警的戰友都請來了,成立個大樂隊,把下邊會演奏的都召集上來排練,到下邊所屬單位演。師父功力很高,但從來不表現的奇奇怪怪、顯示自己我會這個,我會那個。單位裡只是少部份人知道師父能調病,誰有病,找到師父,就給調整調整。有個同事手麻,師父給他調整,手沒挨上,他說就像針扎的一樣。師父告訴我說:「他病太多,得把他的身體劃成塊,一塊一塊的治。」那時候知道師父很有本事。迫害之後,邪黨給師父造謠,雖說大家對佛法、修煉不明白,但都肯定師父不是邪黨宣傳的那樣。
當時我身體不好,肺結核、心臟病、胃病、關節炎、頭疼等,為了好病,我開始練氣功,有很多事就去找師父。師父總是那麼平和,說話很和氣。
練氣功首先得打開勞宮穴,才能納氣、發氣,把身體經絡打開。師父在我手上勞宮穴位置捻了一下,說:「就開這麼大吧,開大了呢,沒有好處,這樣就行了。你練三年也練不開,這回練吧。」我告訴師父我兒子也練氣功,說有時間也給我兒子開一下,師父答應了。二期班時,做周天法,師父走到我兒子跟前,拿起他的手瞅瞅,用手指點住勞宮穴,一擰。我兒子說象綠豆粒似的,手心涼。他是最不敏感的,師父給開穴還體會到,挺激動。
練氣功很多人開了天目,師父在我眉毛上橫著劃了一下,又從腦瓜頂上豎著劃到鼻樑這,我就看見前邊有亮點。師父教我煉天目,瞅著山根部位。我煉一陣就不煉了,師父說不煉那就沒有辦法了。
師父沒傳法前給我講了一件事。上泰國看妹妹時,有一位老闆請師父給他調整治病。當時屋裡坐了不少人,有個人來請師父,直接奔鬍子很長、年紀大的人去了。長鬍子那人告訴說:不是我,是這位年輕人。他一看師父這麼年輕,就懷疑:能有功力嗎?結果師父給病人調整好了。
那天到師父辦公室,看師父在寫稿,說以後要出書。那是91年冬底,師父做卡片、入門證,為辦班傳法做準備工作。
師父常到氣功協會去辦事,有些人開了天目的,這個看這個,那個看那個。師父伸出手來,問你看我這手裡有什麼?一個老太太不吱聲,她卻看見了,說師父手裡托著佛呢!師父跟我說這件事的時候,我就想:佛在師父手裡托著,師父一定比一般的佛都高。因為我家祖上就信佛,原來我就知道修佛修道的事,佛道本來就在人這修,沒什麼大驚小怪的。
平時,師父辦公室鴉雀無聲,別人沒有話,能量在制約一切。師父告訴我:「整個這個樓都受益,都有好處,但他們體會不出來。」
那些年練氣功,雖說有感覺,但提高的也不大。師父說:「氣終歸是氣,沒有制約作用。」那時也不懂是甚麼意思。就這樣師父也沒說你別練那些了,煉我這個吧。有一次,師父看我:本來身體都練開了,怎麼又關上了? 我就想讓師父幫我再打開,師父說得需要挺長時間。這樣吧,你參加我辦的班吧,不收你錢。於是我參加了師父辦的第二期法輪功學習班。
一九九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晚上六點,師父在長春市五中階梯教室辦了二期班,當時能有二百多人。二期班的學員坐在前邊,台階上邊,有一期班的學員,連聽課,帶煉功。
參加班的老年婦女占多數,大多數都是為了祛病的,有練別的氣功的,好多都是佛教居士。師父講課兩個小時,先講一個多小時法,然後再教功。講到關鍵的地方,大家聽不懂的,師父就往黑板上寫寫字。因為整個氣功形勢都是講祛病健身,那時師父是以氣功形式講法的,講深了大家也接受不了。進門時工作人員給每人一個小本,是師父用鉛筆畫的煉功動作圖。煉功動作前邊介紹功理功法,比《中國法輪功(修訂本)》講的還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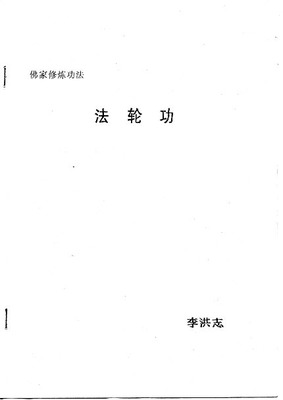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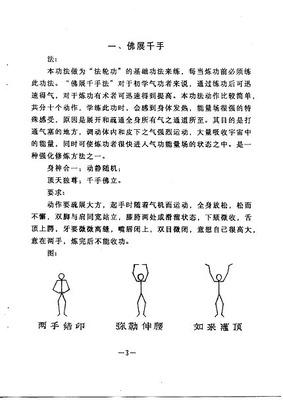
在班上,師父給大家下氣機,因為每個人身體素質不一樣,師父告訴大家:有下的,有沒下的;有下的多,有下的少。我坐在後邊,不知道自己屬於哪種情況,問師父給我下了沒有?師父說:「咋沒給你下呢?還下的最多呢!」
辦班時,師父講,我把你們的元神給調整大了,調到五六歲小孩兒那麼大,沒有危險,不然,有可能就被別的東西給吃了。現在沒事了。師父還告訴大家,遇到不好的東西了,「拿法輪打它」。
有一天,沒講課之前,有個學員的身上有不好的東西,表現不正常,大家圍在那。我們單位一個同事拿了一瓶水,師父喝了口水,撲的往她前身一噴,都是霧。我就在跟前,霧也噴到了我身上。然後師父在她身上「啪啪」的拍給清理。以前聽說過拿水噴霧調病,有人也上廟裡去問過,老和尚說得把水存放一百天,才能噴出霧來,說拿過水就噴出霧來,辦不到。一件事、一件事,讓我看到師父的功力真不一般。
那天在操場上做完法輪周天法往回走時,師父跟我說:「你看見我打手勢沒有?」我說沒注意啊。師父說從上邊來那麼多佛,要下來幫著我照顧照顧,我給他們打手勢,說不用,告訴他們我自己能照顧過來。我明白師父做這件事是有佛幫著的。
我有頭疼病,沒事就睡覺,聽課時一邊聽一邊睡覺。師父說:「別看你們睡覺,你們的元神都可精神了,都扒著頭在那聽。」師父講要清理大腦,使我們處在麻醉狀態,不然受不了。那時對怎樣修煉還不是很清楚。我兒子聽了就是感覺好,也說不出來怎麼好。講完課時師父走到他跟前,他跟師父說:「師父講的真好!」師父表情非常平靜。
九天講課,第十天答疑,學員提問,師父解答。問一個,「又是佛教的。」再問一個,「哎,又是佛教的。」當年的佛教徒有很多就是從這開始走進大法修煉中來了。
二期班辦完後,師父對我說:「講課這屋裡下了氣機,四角都下上了。現在氣機的紅光還在往外冒,有功能的都能看見了,再過多長時間還能看的見。」我問師父能不能收回來。師父說:「不收回來,就放在這了。」師父從北京回來,講到手摸到哪,哪都有能量,說留著,有好處。這些問題後來在各地講法班上師父都講了。之後師父騎著自行車,那是最老式的很破舊的自行車,圍著長春市騎了一圈,給整個長春市清場,下氣機。師父告訴我,「長春市都下上了,在哪兒煉功都沒問題。」從那以後,我放棄了其它氣功,真正煉法輪功了,逐漸懂得什麼是修煉。不到半年,原來的病就都好了。

長空俱樂部
八月九號,那是個星期天,師父在長空俱樂部辦了一場帶功報告,為大家調病,不收錢,義務的,親朋好友的,誰有病都可以去。我是全家一個不落都去了。那天師父到場後,就讓一個用擔架抬著的病人抬到講台上,也沒動什麼手,就讓她從擔架上坐起來,讓她站起來,讓她走一圈,又在台上跑了幾圈,就幾分鐘的工夫,一個癱著的人就好了,全場那個激動啊!我女兒當時天目開著,她看見師父在台上坐著,台下對面有個大佛對著師父,外面還有大佛,比樓還高的佛。師父講了一會兒課,接著打出功來給大家調病,當場見效的人太多了,我們全家的身體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變化。
我家族中祖輩就供一堂「仙」,原來我特別招那些不好的東西,睡覺時黃鼠狼都能把我鼻子咬出兩個牙印、咬出血。家族中的人都有心臟病。老家那有隻狐狸長個犄角,它把犄角往地上一扭,大家都鬧心,我家最重。我上師父家把這事說了,想讓師父幫著處理一下。師父答應了。後來聽妹妹說,一隻老雕追那隻狐狸,狐狸被攆的跑到三妹家鍋台後,被老雕給叼著飛走了。師父把那些不好的東西給清理了。從那以後,我們家族人的心臟病就都好了,後來家族中的人也大都修煉大法了。
我練了幾年氣功,只是在動作上下功夫,沒什麼長進。漸漸的知道了法輪功和其它氣功不一樣,要同化宇宙特性「真、善、忍」,要重「心性」修煉,要求煉功人有極高的「德」,「欲正其心,先誠其意」。
以後師父在長春講法我都去,聽幾天,聽不全。有一陣,總覺得有個東西在眼皮上跳,繞著兩隻眼睛轉圈,再爬到鼻子尖上,鑽到鼻子眼這耷拉著。我問師父這是什麼。師父仔細的瞅了瞅,拍了拍我的肩膀高興的說:「不錯,煉出條小龍來了。」煉法輪功半年多,這麼短的時間就修出生命體來了,師父高興,我也高興。可它在我身體裡四處竄,疼不是疼,癢不是癢的。真正走進修煉,大家各種狀態都有,就去問師父。師父在《為長春法輪大法輔導員講法》中告訴我們:這些生命「在更高層次中也有,它一般不是修上去的,它是在那個自然環境中產生的。在高層次修煉的人身體產生的龍等生命體當然是你的,也就隨你的圓滿而去高層了。」師父什麼都知道,什麼都能說清楚。

吉林大學正門(解放大路)
師父在《轉法輪》中講:「我們上次在吉林大學辦班時,有個學員從吉林大學正門出去,推個車子,剛走到中間,兩輛轎車一下子就把他夾在中間,眼看就要撞上了,可是他一點都沒有害怕。我們往往遇到這種事情都不害怕,在那一瞬間,車就停住了,沒有出現問題。」這件事說的就是我。那是九四年五月長春七期班(白天班)散場,我最後從鳴放宮出來,走到吉林大學正門,看見師父站在大門口。我過解放大路快車道,正推著車子走到中間,東西兩邊兩輛轎車一下就把我夾在中間,就要撞上了,車一下就停住了。我也沒害怕,走到慢行道,回頭看看,師父站在大門東側人行道上,還在那看著我呢。當時我並不明白怎麼回事,九五年初,《轉法輪》出版了,一看書才明白,那次是取命來了,師父保護了我,我還了一次命債。
九三年以後,師父全國各地四處傳法,不能在單位全天上班,所以辦了停薪留職手續。九五年師父到國外傳法,再見到師父就不容易了。一次,師父從國外回來,在地質宮接見學員,跟我兒子說:「告訴給你爸帶個好。」和大家說了一會話,師父又說:「給你爸帶個好。」說了三遍。師父還惦記著我,惦記著家鄉的父老鄉親,更惦記和師父有近緣的親朋好友。
十幾年了,我很惦記師父,打聽師父的一切消息,盼著迫害早一天結束,盼著師父早一天回來。
(明慧網)


